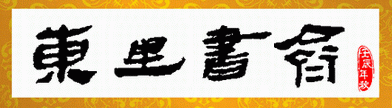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【會校崇禎廿卷本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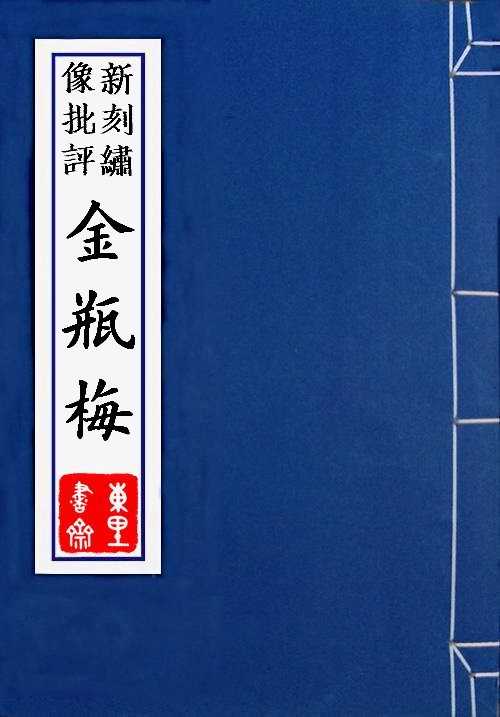
——以上摘自石昌渝主編《中國古代小說總目·白話卷》(山西教育出版社西元2004年版)。
香港三聯書店有會校本,當即此文本。按原文本「閒」多作「閑」,今爲便於分別,多有改動,如將「幫閑」改爲「幫閒」,「等閑」改爲「等閒」之類。每回前之繡像,本站取自臺灣增你智版《金瓶梅詞話》(其底本爲萬曆丁巳本《詞話》,《詞話》原無插圖,出版時于每回之前補入崇禎本繡像。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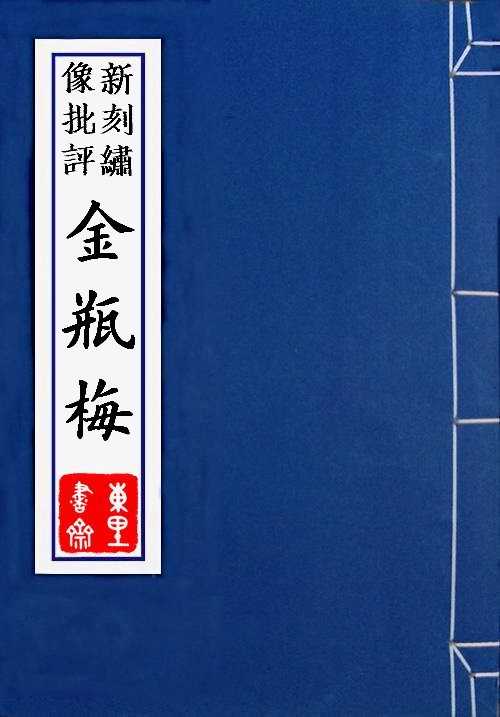
金瓶梅一百回 (明)蘭陵笑笑生撰
現知明刊本《金瓶梅》有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十卷本及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二十卷本,前者卷十回,後者卷五回,皆爲一百回。蘭陵笑笑生撰。兩本皆有東吳弄珠客序及廿公跋,十卷本又有欣欣子序。笑笑生、弄珠客、欣欣子、廿公諸人皆無考。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學界有數十種說法,可分爲作家個人創作和藝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兩大類。以爲文士創作的指姓道名,並加論證的已有三四十種,其中重要的有:
(一)王世貞說 世貞字元美,號鳳洲、弇州山人。太倉人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進士,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,刑部尚書。其父王忬(1507一1560)爲名將,進右都御史,爲嚴篙(1480一1567)父子構害。嚴篙死,方獲平反。世貞爲著名文學家,爲文學復古運動主將,著有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。王世貞爲(金瓶梅》作者說產生最早,影響最大。沈德符(字景倩,1578~1642)在他的《萬曆野獲編》已有“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,指斥時事”的說法。萬曆年間,屠本峻和謝肇淛已提到王世貞家曾藏有全本《金瓶梅》。清初版《玉嬌梨》之“緣起”謂“《玉嬌梨》與《金瓶梅》,相傳出弇州門客筆,而弇州集大成者”云云。康熙十二年(1673)序刊本宋起鳳《稗說》卷三“王弇州著作”條則謂:“世知《四部稿》爲弇州先生生平著作,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一書,也先生中年筆也。”並及王世貞爲報父冤憤而作此書,非其門客所作也。張竹坡批本《金瓶梅》,首冠康熙乙亥(l695)謝頤《第一奇書序》,亦謂“《金瓶》一書,傳爲鳳洲門人之作也,或云即鳳洲手”。張批本且有“苦孝說”,爲鳳洲說進一解。因張評本《金瓶梅》清代大爲流行,王世貞說遂得廣泛傳播,又有很多筆記繪影繪風,推波助瀾,此說遂風靡一世。至近代,有吳晗等考證此說之無據,因又沉寂。近年朱星及周鈞韜等,推翻吳氏之考證,重新提倡王世貞說。周鈞韜又發展出王世貞和他的門人聯合創作說(參見《金瓶梅探謎與藝術賞析》,長春,吉林文史出版社,1990)。
(二)李開先(1502一1568)說 開先字伯華,號中麓、中麓放客,山東章丘人。嘉靖八年(1529)進士,官至太常寺少卿。開先爲著名文學家,精詞曲,酷愛俗文學。著有散曲集《一笑散》、《傍妝臺百首》,傳奇《寶劍記》,詞曲評《詞謔》,詩文集《閒居集》等。吳曉鈴於1962年提出此說,80年代後又多次爲文證之。他指出“《金瓶梅詞話》在徵引戲曲作品時,總是把劇名標舉出來,但有一個例外,那就是李開先的《寶劍記傳奇》,從沒有標舉劇名,儘管全書徵引《寶劍記》不下十七次(這只是我到目前所能發現的數字)”(《〈新刻金瓶梅詞話〉和李開先的〈寶劍記傳奇〉比較研究》載《明報月刊》1989年7月號,第110一114頁)。卜鍵撰有《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》(甘肅人民出版社,1988)一書,肯定此說。
(三)屠隆(1542一1605)說 屠隆字長卿、緯真,,號赤水、鴻苞居士。鄞縣(今浙江寧波)人。萬曆五年(1577)進士,歷官至禮部郎中,以事罷歸。文學家,著有傳奇《曇花記》、《修文記》、《彩毫記》,詩文集《白榆集》、《由拳集》、《采真集》、《南遊集》等。黃霖有《〈金瓶梅〉作者屠隆考》(載《復旦學報》社會科學版,1983年第3期)及《〈金瓶梅〉作者屠隆續考》(載《復旦學報》社會科學版,1984年第5期)提出此說,以《金瓶梅》第五十六回“哀頭巾詩”及“祭頭巾文”見明代通俗類書《開卷一笑》(後稱《山中一夕話》)中,此書卷一題“卓吾先生編次、笑笑先生增訂、哈哈道人校閱”,其卷三題作“卓吾先生編次、一衲道人屠隆參閱”,由此推論“笑笑先生、哈哈道士、一衲道人、屠隆都是同一人”。魏子云、鄭閏皆贊成此說。
除此之外,還有張遠芬的賈三近(1543一1592)說(《金瓶梅新證》,濟南,齊魯書社,1984)芮效衛(David Tod Roy)的湯顯祖(1550一1616)說(《湯顯祖創作〈金瓶梅〉考》,載《金瓶梅西方論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)。王螢、王連洲的謝榛(1495一1575)主筆,鄭若庸、趙康王朱厚煜參預說(《〈金瓶梅〉作者之謎》,載《金瓶梅作者之謎》,寧夏人民出版社,1988)。葉桂桐、閻增山的李先芳(1511一1594)說(《李先芳與金瓶梅》,寧夏人民出版社,1988)。陳昌恆的馮夢龍(1574一1646)說(《〈金瓶梅〉作者馮夢龍考》,載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》社科版,1988)。馬征、魯歌的王穉登(1535一1612)說(《〈金瓶梅〉作者王穉登考》,載《社會科學研究》1988年第4期)。孫楷第提出,趙興勤證成的馮惟敏(1511一1580 ?)說(《也談〈金瓶梅〉作者及其成書時間》,見《金瓶梅研究集》,濟南,齊魯書社,1988)。朱恆夫的唐寅(1470一1523)說(《〈金瓶梅〉作者唐寅初考》,載《江蘇教育學院學報》社科版,1994年第3期)。此外還有徐渭(1521一1593)、沈德符、陶望齡、丁耀亢、丘志充等說。明清人所提出的趙南星(1550一1627)或薛應旂(l550在世)說(宮偉鏐(春雨草堂別集》),盧楠(1540在世)說(滿文譯本《金瓶梅·序》)等,也引起注意。
早在40年代,馮玩君的《〈金瓶梅詞話〉中的文學史料》(見《古劇說匯》,上海,商務印書館,1947)即已注意到《金瓶梅》的話本性質。《詞話本》不單在名稱上顯示出他是說話人(或稱書會才人)所創作的,正文的情況亦如此。我們看到書中採用大量的書會留文,說書人常用的套話,引用大量前代和當代的戲曲,引用時常祇寫出首句,而以“云云”代表全文,這是寫給同樣熟悉這些戲曲的行家看的,而不是爲一般讀者。至於在書信後的署名前加“下書”兩字,也是說書人的習慣,表明這原是爲說的語言,而非爲看的文字。《詞話本》的敘述方式也異乎文人創作小說,如語言中的贅詞;如將一個人的說話分成數段,加上“又問道”、“因道”等詞連接;如多人對話,不指明講述者;如在較長的對話中轉換第三人稱的身分爲第二人稱之類。凡此等等都是講唱文學敘述方面因“聽”的特性而發展出來的(參見梅節《“金學”的海洋歷險者》,載周鈞韜、魯歌主編《我與金瓶梅》,成都出版社,1991,第126一143頁;又參見傅憎享《〈金瓶梅〉話本內證》,載《金瓶梅研究》第四輯,1993,第189一203頁)。如果說“套語”、“云云”、“下書”之類祇是外在的形式,作者模仿話本的形式從事創作,亦可以做出來的。而書面文學和講唱文學不同的敘述方式則不是可以模仿出來的。從《詞話本》到《說散本》、《張評本》的改動中,很重要的一點是敘述方式從講唱文學向案頭文學的轉變。孫遜指出:“從小說的回目、詩詞以及人物場面等幾個方面的‘內證’,《金瓶梅》更可能是中下層社會書會才人一類人物所寫,這種人文化修養不很高,但狀物摹神的本領卻特別高,他們擅於描寫渲染,卻不善於語言文字的推敲提煉,因此《金瓶梅》一方面散文部分描寫生動,另一方面韻文部分則相形見細;同時即使散文部分,由於缺少提煉,總不免給人生動有餘而精煉不足的感受。對於筆下人物,作者更熟悉的也是中下層社會的形形色色,描寫起他們來繪聲繪色,遊刃有餘,而對上層社會的人物則不免捉襟見肘,顯得力不從心。”(《一蓑風雨任生平》,《我與金瓶梅》,頁20)陳益源發現《金瓶梅詞話》第五十九至第八十回抄改襲用明代中篇傳奇《懷春雅集》十九首詩和一闕詞,其中失律出韻,又和書中情境不配合的情況,否定了《金瓶梅》是“嘉靖間大名士手筆”說(《〈懷春雅集〉考》,載《金瓶梅研究》第五輯,1994,第129一150頁)。也可爲書會才人創作說加一旁證吧。《金瓶梅詞話》是書會才人的創作這一觀點在學術界中很有代表性,趙景深、王利器、梅節、陳詔、孫遜、傅憎享、徐扶明等都持有相同的觀點。戴鴻森的劉九說(《我心目中的〈金瓶梅詞話〉作者》,載《讀書》1985年第4期),亦可列人此一類。
由此出發,又發展出《金瓶梅》是“藝人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”的觀點。50年代,潘開沛在《〈金瓶梅〉的產生和作者》(《光明日報》1954年8月29日)一文中指出《金瓶梅》“不是哪一個‘大名士’、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裏創作出來的,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裏的許多藝人集體創作出來的,是一部集體的創作,祇不過最後經過了文人的潤色和加工而已”。80年代起,徐朔方是此一觀點的重要論證者,蔡敦勇、程毅中等亦贊成此說。徐朔方又提出《〈金瓶梅〉的寫定者是李開先》(載《杭州大學學報》社會科學版,1980年第1期)。他設想:“《水滸》故事當元代及明初在民間流傳時,各家說話人在大同之中有着小異,其中一個異點,即爲迎合封建城市的市民階層和地主階級的趣味及愛好,西門慶的故事終於由附庸而成大國,最後產生了獨立的《金瓶梅詞話》。它和《水滸》一樣,都是民間說話藝人在世代流傳中形成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,帶有宋元明不同時代的烙印。”(《〈金瓶梅〉成書新探》,載《中華文史論叢》1984年第三輯,第172頁)他後來將李開先寫定說改爲:“《金瓶梅》的寫定者或寫定者之一是李開先或他的崇信者。祇有他本人或他在戲曲評論和實踐上的志同道合的追隨者,他們可能是友人,或一方是後輩或私淑弟子,纔能符合上述情況。”(《徐朔方集·自序》,杭州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3,第一卷,第6頁)王利器也是李開先改定說的支持者(參見《〈金瓶梅〉的改定者是誰?》,載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93年第六期,第266一278頁)。劉輝則認爲《金瓶梅詞話》是“一部完整的未經文人寫定的民間藝人說唱‘底本’”。他發現“首圖本”第一百零一頁插圖爲詞,署“回道人題”,指出回道人爲李漁化名。再據張竹坡評本“第一奇書”《金瓶梅》皆署“李笠翁先生著”,而李漁爲張竹坡父執,因證明李漁爲“廿卷本”《金瓶梅》的寫定者(見《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》,瀋陽,遼寧人民出版社,1956,第36、74一78頁)。在民間故事和俗文學中,回道人是八仙之一呂洞賓遊戲人間所用的化名,不一定要和李漁扯上關係。王汝梅查出“首圖本”上回道人的題詞,爲《全唐詩》第八五九卷所收的呂洞賓《漁父詞》十八首中的第十六、十七首,就時間來論,李漁不可能是崇禎刊本《金瓶梅》的評改者(《李漁評改〈金瓶梅〉考辨》,載《吉林大學學報》1992年第5期)。
以目前資料看來,找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自是徒勞。既認爲《金瓶梅詞話》是書會才人的創作,而又要找寫定者或評改者,也是白費氣力的工作。徐朔方自李開先寫定說,到不相信大名士的過多參與,改爲李開先“崇信者”或“私淑弟子”寫定說,和不知名的人寫定已沒甚麼不同了。既然《金瓶梅》中引用了李開先《寶劍記》最少十七處,則說作者或寫定者是李開先的私淑弟子也無不可,這倒是一個自圓的說法。但歸根到底,還是要找個人頭。而且又何必將演唱的藝人和寫定者截然分開?能創作、演唱的人是藝人雖非大名士,但記下詞話本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古代的說話人是民間文化的傳播者,扮演着娛樂者和教育者雙重身分,當時書會才人、名公其實是下層的知識分子,完全能夠執筆爲文的。
“藝人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”說是從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及話本小說從講說到成書過程中所歸納出來的理論,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古代小說形成的瞭解。但“集體創作”的提法,比較適合於民間文學而不太符合俗文藝的創作情況。講唱文學注重傳承。設想某種詞話是由某一天才藝人在長期的講唱生涯中,慢慢創造出來的。按講唱傳統,詞話中用了各種俗文藝的“留文”,創作者在不斷的演唱中對故事加以增改,依照不同的演唱場合在細節上有所增刪,漸漸形成一套完整的故事,故事的基本結構,人物和人物的性格相對穩定。在創造之初,這一話本是屬於某一藝人,慢慢擴大到某一門戶(如此一師傅帶有徒弟或此人之家屬之類),甚至某一書會成員所有。和民間文學不同,在俗文學中,特別是長篇的史詩小說中,傳承者是非常講究家法的。除非遇到特殊的天才,對承繼的傳統加以豐富和發展,一般則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,增刪細節,使更符合講演的時代和場合。祇有在長期的傳承中,如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之類,纔會成爲很多講唱藝人公共的題材。即使此時,各家還有各家的家法,各家的特點,而不是集體公共的產品。我們來看《金瓶梅詞話》。《金瓶梅詞話》雖採用很多前代文獻資料及書會留文,此書雖以北宋末年爲背景,但實際描述的是明嘉靖年間(1522一1566)社會,因此此故事創作不會早於嘉靖,而最遲到萬曆二十年(1592)即已成書,由創作到成書時間不長,如經演唱,也祇在一兩代藝人之間,和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的世代流傳不同。《金瓶梅詞話》也許就出自創作、講唱的藝人之手,談不上甚麼集體創作。即已由不祇一個、不祇一代的藝人講述,還祇在某一書會,某個師承或家庭傳承下講唱的。
有人認爲目前並“沒有絲毫史料”可以說明《金瓶梅》是世代累積型的作品(參見孟昭連《〈金瓶梅〉是“世代積累型”作品嗎?》,載《明清小說研究》1993年第四輯,第89一105頁)。蒲安迪以爲“《金瓶梅》全書首尾相應的連續結構,在一回一回銜接之處很少見到那種‘未知如何……’式的緊張處,更不像一種由說書一場一場的獨立回目組成的章回連環故事。而且,徐朔方也指出,《金瓶梅》那種特殊的內容細節顯然不太適合於公開口頭表演的敘述形式”(《〈金瓶梅〉非“集體創作”》,載《金瓶梅研究》第二輯,1991,第82一90頁)。說《金瓶梅》不是世代累積的集體創作、不適合表演,並不能否定《詞話本》的話本特徵和它是藝人創作的論證,更不能因此得出《金瓶梅》爲文人作品的結論。某一天才的說書人,以他習慣的說書形式和語言,寫出《金瓶梅詞話》,也不一定要經過演唱後再來記錄的。究竟《金瓶梅詞話》有沒有經過演唱的階段?是直接書面創作還是先經演唱再紀錄下來的作品?還是有待探討的問題。
就內容反映的時代來看,《金瓶梅詞話》產生於嘉靖年間。從其中從第六十一回起大量引用李開先《寶劍記》,而前六十回則無一處道及一事推測,前半部或成形於《寶劍記》流傳以前,後半部或成於《寶劍記》盛行以後。寫定成書,自然是嘉靖二十六年(1547)《寶劍記》脫稿之後。目前對《金瓶梅詞話》引用各種資料,特別是俗文學資料的研究仍不充分,未來的研究或者會將成書年代更推後些。目前所知,萬曆二十年(1592)左右,已有《金瓶梅》抄本在文士圈中流傳,則其寫定,又應在此時之前。也許隨着研究的深人,我們還可將《金瓶梅》抄本出現時間,推得更早更準確些。
此書自《水滸傳》武松殺西門慶、潘金蓮爲兄武大報仇故事敷衍而出,取書中主角西門慶妾潘金蓮、李瓶兒及婢龐春梅三人名中一字,合爲書名。敘北宋徽宗年間,山東清河縣破落戶財主西門慶勾官結府,巧取豪奪,娶了六房妻妾,頓成鉅富。又以財富賄賂,夤緣爲清河縣掌刑副千戶,後升爲千戶。以官營私,大富大貴。壯年時以縱淫過度暴斃,家道衰落,諸妾及家人散去,惟存妻吳月娘守遺腹子孝哥。後金兵南侵,逃亡途中孝哥出家。月娘收僕人玳安爲義子承西門家業,七十而亡。
《金瓶梅》是中國第一部以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爲題材的長篇小說。故事雖託言於北宋,而所寫實爲明代,特別是嘉靖一朝。以西門一家爲中心,擴展至市井、至社會各階層。所寫有地痞流氓、無賴潑皮、販夫走卒、僧道醫卜、三姑六婆、文士官吏,乃至帝王將相,而着意寫家庭婦女及家庭之日常生活,開啓了後來明清人情小說的大流。其敘事寫人,多用白描,即以客觀描述,以代替過去說話方式的主觀描述。其敘述方式,亦由既往的白話長篇的聯綴式變爲單體式,由線性結構變爲網狀結構。
傳世明刊《金瓶梅》有下列兩種系統之版本:
(一)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十卷,卷十回,共一百回。簡稱爲“詞話本”、“十卷本”;因其中有“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”序,故又稱“萬曆本”。首《金瓶梅詞話序》,謂“蘭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傳》”云云,稱笑笑生爲其友。末署“欣欣子書於明賢里之軒”。次《〈金瓶梅〉序》,謂:“《金瓶梅》穢書也。袁石公巫稱之,亦自寄其牢騷耳,非有取於《金瓶梅》也。”又引其友褚孝秀之言。石公爲袁宏道(1568一1610)號,褚孝秀無考。次爲《跋》,署“廿公書”,謂“《金瓶梅傳》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,蓋有所刺也”云云。接下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詞四闕及酒色財氣《四貪詞》。下《新刻金瓶梅詞話目錄》,一百回,不分卷。正文半葉十一行,行二十四字。四周單框,絲闌。版心單白魚尾,上作“金瓶梅詞話”,下爲回次,葉次。此書現存全本三部,殘本一帙。除一部藏中國外,餘藏日本。原北平圖書館所藏一部,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。此本欠第五十二回第七、第八兩葉,上有若干後人批語及改文。1933年馬廉等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,影印本增入通州王孝慈所藏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插圖二百幅,並以此本補抄所缺兩葉;又修去後人批語及改動正文。此影印本後又經多次再影印。日本方面,日光慈眼堂藏本最爲完整。山口縣德山市毛利書庫棲息堂藏本(簡稱《棲息堂本》)缺第二十六回第九葉、第八十六回第十五葉、第九十四回第五葉;第五回末葉(第九葉)文字與慈眼堂本不同。殘本存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,原爲《普陀洛山志》襯紙,存二百二十五面,分裝三冊。所存者爲第十一至十三、第十五、第四十一至四十八、第八十八至第九十四回,除第十一、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五、八十五、九十一、九十二回完整外,餘皆殘缺。據比勘可知,現存四種《詞話》本皆同一版本,惟《棲息堂本》第五回末葉爲後刻補入者。據研究此本印行較遲,缺此一葉,遂據《忠義水滸傳》第二十五回補刻者。是知《詞話》本最少有兩次印刷。1963年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據《慈眼堂本》和《棲息堂本》配合影印,並附《棲息堂本》第五回末葉。書末附《日光本採用表》,列出所使用《慈眼堂本》葉次;又有《修正表》,於原本文字不清晰處,據其他各本校出。正文共五冊,第六冊爲《清宮珍寶皕美圖》。大安本爲最可靠的《詞話本》影印本,曾多次被影印,但影印本多缺附錄部分。當代的《詞話本》整理本或是不全,或經刪節,惟梅節校訂,陳詔、黃霖註釋之《金瓶梅詞話》(香港,夢梅館,1993)爲全本,且校勘最精。《詞話本》除所知三種明刊本外,又有傅惜華藏殘本,書名爲《繡像古本八才子詞話》,存五冊十七回,前有順治二年(1645)序及目錄,知爲十卷百回本。此本已佚,是否爲此一系統本子,亦不能知。
(二)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,計二十卷,卷五回,共一百回。相對於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,此本有繡像,有評語,又少了很多說唱的成份,更接近案頭讀物,故簡稱爲“說散本”、“像評本”、“廿卷本”、“繡像本”、“評改本”等;又因正文“由”作“繇”、“檢”作“簡”,避崇禎諱,故又稱“崇禎本”。此本現所知者,中國有王孝慈藏本(下稱《王氏本》)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(下稱《北大本》)、首都圖書館藏本(下稱《首圖本》)、天津圖書館藏本(下稱《天圖本》)、上海圖書館兩種藏本(下稱《上圖甲本》、《上圖乙本》)、周越然藏本(下稱《周氏本》)及吳曉鈴藏抄本(下稱《吳抄本》)等,又有若干殘本,惟情況不詳。以上諸本中,《周氏本》亦佚去,祇存一書影及簡單的版本記錄。《吳抄本》據研究者謂抄於乾隆年間,爲刪節本。日本方面有內閣文庫(下稱《內閣本》)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(下稱《東大本》)、天理大學中央圖書館(下稱《天大本》)三處藏書。《北大本》(北京大學出版社,1988)及《內閣本》(臺北,天一出版社,1985)皆曾影印。現將各版本資料簡介如下:
(甲)《王氏本》 通州王孝慈原藏,現已佚去。此本插圖曾影印入古佚小說刊行會所出版的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中,其第一回首葉及部分插圖又影印入鄭振鐸編《世界文庫·金瓶梅詞話》中,前三十三迴文字亦校入鄭編本。鄭振鐸謂此本“插圖,凡一百頁,都是出於當時新安名手。圖中署名的有劉應祖、劉啓先(疑爲一人)、洪國良、黃子立、黃汝耀諸人。他們都是爲杭州各書店刻圖的,昊騷合編便出於他們之手。黃子立又曾爲陳老蓮刻九歌圖和葉子格。這可見這部金瓶梅也當是杭州版。其刊行的時代,則當爲崇禎間”。又謂此本有東吳弄珠客的序文(《中國文學研究》,北京,作家出版社,1957,第257頁)。此本正文半葉十行,行二十二字。眉批每行二字。據黃霖謂“上圖乙本的正文及眉批接近王氏本,又其插圖、正文的刊刻較爲粗劣的情況來看,它當是王氏本的翻刻本”(《關於〈金瓶梅〉崇禎本的若干問題》,載《金瓶梅研究》第一輯,1990,第60頁)。
(乙)《北大本》 馬廉原藏,上有“不登大雅之堂”陰文方章。缺扉葉。首《金瓶梅序》,署“東吳弄珠客題”。次《新刻批評繡像金瓶梅目錄》。各回前有插圖一葉,全書計一百葉。插圖同《王氏本》而較粗簡。正文半葉十行,行二十二字。有眉批、夾批,眉批每行四字。《天大本》格式與此相同,然有個別文字不同,自不能謂爲同版。其插圖合爲一冊,可能爲後人改裝的結果。上圖甲本形式亦類此本,亦有個別文字相異,彼此關係仍有待研究。
(丙)《內閣本》 扉葉右上方小字作“新鐫繡像批評原本”,版中大字作“金瓶梅”,左上方稍低處作“本衙藏本”,下有瓶插梅花圖。卷首有《金瓶梅序》,署“東吳弄珠客題”,又有廿公跋,有插圖五十葉,一百幅,每回一幅,合置書前,惜已散佚。接下爲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目錄》。正文半葉十一行,行二十八字。有眉批、行間夾批。眉批三字一行,然亦有二字一行者。正文首回首葉首行作“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”,字稍大。第二行爲回次回目。《東大本》被研究者認爲與《內閣本》同一版本的本子,其書前插圖五十葉亦已佚失。此外又有《首圖本》,其正文形式與《內閣本》相同,文字亦最相近,惟無眉批,且刊刻較差,故疑爲《內閣本》之翻刻本。《首圖本》現缺一冊(卷十一,第五十一至五十五回)。書前有插圖一冊,一百零一頁,前百頁皆據他本轉刻而甚粗劣,且刪去原刻者署名。末一頁爲回道人題詞。
《周氏本》、《上圖乙本》及《天圖本》其正文格式亦同《王氏本》。《周氏本》已佚,據記載,有插圖一冊,百葉。未知其眉批情況。《上圖乙本》插圖亦如《周氏本》,百葉,合爲一冊,置書前。其正文近《世界文庫本》,眉批或二字一行,或四字一行,較《北大本》少了很多批語。《天圖本》插圖如《北大本》,分置各回前。正文及眉批近《上圖乙本》,惟眉批較多。此三種可合爲一類,視爲《王氏本》之再刊本。現所知道的“廿卷本”達十多種,此外還有若干殘本(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北大圖書館皆有殘本),因分藏各處,閱讀不易,各版本間之關係,至今仍未有全面研究。當代校點整理完整的“廿卷本”有齊煙、汝梅校點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(濟南,齊魯書社,1989)。“廿卷本”版本雖多,就正文而言,相差還是有限的。目前研究結果,就插圖、評語和正文形式一一推究,發現《王氏本》最近原刊本。
張竹坡(名道深,1670一1698)評點的《第一奇書金瓶梅》(下稱《張評本》)在《金瓶梅》的流傳史中十分重要,此書於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出版,以後有許許多多的重刊本、刪節本。在1932年翻印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以前,社會流傳的幾乎都是《張評本》或他的增刪本,滿文和其他文字的《金瓶梅》譯本,也是以(張評本》爲底本的。現存的“本衙藏版”本,一般認爲原刊本。扉葉框內右上方作“彭城張竹坡批評金瓶梅”,中間大字“第一奇書”,左下方作“本衙藏板,翻印必究”。首《第一奇書序》,署“時康熙歲次乙亥(三十四年,1695)清明中浣秦中覺天者謝頤題於皋鶴堂”。謝頤爲張潮(1650一?)的化名。次《第一奇書凡例》、《雜錄》、《竹坡閒話》、《冷熱金針》、《<金瓶梅>寓意說》、《苦孝說》、《第一奇書〈金瓶梅〉趣談》、《批評第一奇書〈金瓶梅〉讀法》等。各回正文前有總評,另葉刊出,置正文前。《張評本》有眉批、夾批及雙行批註。正文四周單框,半葉十行,行二十二字。版心無魚尾,上作“第一奇書”,下爲回次、葉次。又有模刻祟禎“廿卷本”插圖一百葉,另冊裝出。《張評本》據崇禎初刊或較早翻刻本的“廿卷本”如《王氏本》、《北大本》爲底本加評,有些評語引用“廿卷本”的評語再加評論的。所謂“原評”云云,指的就是“廿卷本”的評。《張評本》正文相當忠實原底本,甚至“廿卷本”錯誤的地方,兩本亦同誤。祇有極少數“廿卷本”有明顯錯失的地方作修正,此外就是改去底本上清朝的礙諱字,如“虜患”作“邊患”、“夷狄”作“邊境”之類。故就校勘《詞話本》而言,此本沒有特殊的價值。王汝梅、李昭恂、於鳳樹校點的《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(濟南,齊魯書社,1987)爲較好的《張評本》當代整理本。
廿卷本《金瓶梅》和十卷本《金瓶梅詞話》故事人物絕大部分相同,文字有七成完全一樣,甚至很多錯字都一樣,可知同出一源。但此兩系統的本子又有下列明顯的差別:
第一,“十卷本”卷首的欣欣子序不見於“廿卷本”,也沒有正文前的詞四首和《四貪詞》。
第二,“十卷本”的回目雖每回兩句,但有時字數不等,且不對偶;“廿卷本”則爲比較工整的聯語。
第三,“十卷本”各回開頭雜用詩、詞不一,多引自當代話本如《水滸傳》等,有時重複使用,不少與該回內容無關;“廿卷本”則用詞,多引用《草堂詩餘》等當代流行詞集。
第四,“十卷本”第一回從武松打虎談起,抄自《水滸傳》,“廿卷本”則從西門慶結十兄弟起。“十卷本”第八十四回又有涉及梁山好漢的故事,“廿卷本”刪去,看出改編者要擺脫《水滸傳》影響的努力。
第五,第五十三及第五十四回內容和文字有較大的分別。“十卷本”此兩回寫得比較細膩,和全書較統一;“廿卷本”此兩回草率,和第五十五、六、七回較爲相近,和全書不大接續。
第六,各回皆有刪改,刪去大量詞話的成份(如敘事形式、韻文部分、引用別種書籍或話本部分)並加修飾,又刪改一些方言詞爲普通詞語,使詞話本變成閱讀的本子。
“廿卷本”原自詞話本是大家公認的事實,目前所存“廿卷本”中,還留下不少痕跡。如《北大本》、《上圖乙本》、《天大本》第九卷題作《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詞話卷之九》之類。一般認爲,“廿卷本”是據刊本“十卷本”修訂而成的,“十卷本”是“廿卷本”的母本,他們間是父子的關係。但這不符合兩個版本間的實際情況。首先,要是“廿卷本”自“十卷本”而來,爲甚麼將描述比較細膩又和全書文字風格比較統一的第五十三、五十四回改得面目全非,粗率不堪?其次,就兩種版本互相校勘的結果來看,兩本同引用他書(如《水滸傳》)的地方,間有“十卷本”錯漏處“廿卷本”不錯,又有些“十卷本”脫行、錯簡的地方,“廿卷本”不誤,這都不是父子本說所能解決的。韓南(Patrick Hanan)早就注意到這種情況,認爲“廿卷本”非源於“十卷本”。梅節細校過此兩種版本,他據大量的校勘證明“十卷本”和“廿卷本”是兄弟本而非父子本。黃霖亦看到父子本說不能解釋一些校勘提出的問題,“我認爲崇禎本當以已刊詞話本(所謂‘原本’)爲底本,又參照了另一‘元本’修改加評而成”。這也就間接否定父子本說了。梅節的結論是:“說散本和詞話本的關係雖異常密切,但並非改編自今本詞話。它們可能源自一個共同的祖本。這一點可以說明它們衆多的相肖之處。但兩本在各自流傳的過程中,由於傳抄的訛奪、藏者的是正、編者的刪改等等,又出現不少歧義。其中有些具有可溯性,有些卻不能,後者構成了說散本與今本詞話的質的差別。簡單說,它們是兄弟關係或叔侄關係,而不是父子關係。”(《金瓶梅詞話與說散本關係考校》,載《金瓶梅藝術世界》,長春,吉林大學出版社,1991)
萬曆二十年(1592)間,抄本《金瓶梅》已在一些文人圈中流傳。據文獻記載,最早讀到此書的有著名書畫家董其昌(字玄宰,號思白,1555一1636)、著名文士、醫家王肯堂(字宇泰,1549一1613)和著名文士王穉登(字百穀,1535一1612)等人。袁宏道(字中郎,號石公,1568一1610)於萬曆二十三年(1595)給董其昌的信即詢:“《金瓶梅》從何得來?伏枕略觀,雲霞滿紙,勝於枚生《七發》多矣。後段在何處抄竟,當於何處倒換?幸一的示。”(《袁中郎先生全集》卷二十一《尺犢·董思白》)袁中道(字小修,1570一1624)記其於萬曆二十五年(1597)“往晤董太史思白,共說小說之佳者。思白日:‘近有一小說,名《金瓶梅》,極佳。’予私識之。後從中郎真州(1597),見此書之半。大約模寫兒女情態具備,乃從《水滸傳》潘金蓮演出一支。所云‘金’者,即金蓮也;‘瓶’者,李瓶兒也;‘梅’者,春梅婢也。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,延一紹興老儒於家,老儒無事,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。以西門慶影其主人,以餘影其諸姬;瑣碎中有無限煙波,亦非慧人不能。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:‘決當焚之。’以今思之,不必焚,不必崇,聽之而已;焚之也有存之者,非人之力所能消除。但《水滸》,崇之則誨盜,此書則誨淫。有名教之思者,何必務爲新奇,以驚愚而蠢俗乎?”(《珂雪齋集·珂雪齋遊居柿錄》卷九)萬曆三十四年(1606)袁宏道作《觴政》,其《十之掌故》云:“凡六經、《語》、《孟》所言飲式,皆酒經也。……《蒙莊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南北史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世說》、《顏氏家訓》,陶靖節、李、杜、白香山、蘇玉局、陸放翁諸集爲外典。詩餘則柳舍人、辛稼軒等,樂府則董解元、王實甫、馬東籬、高則誠等,傳奇則《水滸傳》、《金瓶梅》等爲逸典。不熟此典者,保面甕腸,非飲徒也。”則與中郎酒會者,自然都要讀《金瓶梅》了。中郎是當日青年一輩文人的領袖,可能由於他的提倡,促進了抄本《金瓶梅》的流通。屠本畯(字田叔,1542—1622後)在《山林經濟籍·經部》卷八《燕史固書第十二》引上文曰:“不審古今名飲者,曾見石公所稱‘逸曲’否?按《金瓶梅》流傳海內甚少,書帙與《水滸傳》相埒。相傳爲嘉靖時,有人爲陸都督炳(1510一1560))誣奏,朝廷籍其家,其人沉冤,託之《金瓶梅》。王大司寇鳳洲(名世貞,字元美,1526一1590)先生家藏全書,今已失散。往年餘過金壇,王太守宇泰出此,云以重貲遘抄本二帙。予讀之,語句宛似羅貫中筆。復從王徵君百穀家,又見抄本二帙,恨不得睹其全。如石公而存是書,不爲託之空言也。否則,石公未免保面甕腸。”(萬曆戊申1680自序,惇德堂刊本)其實中郎有《金瓶梅》抄本,祇是不全。
萬曆三十五年(1607),袁宏道給他過去葡萄社的社友謝肇淛(字在杭,1567一1624)寫信約晤,謂“仁兄近況何似?《金瓶梅》料已成誦,何久不見還也?”(《袁宏道集箋註》卷五十五《與謝在杭》)謝肇淛後來寫《〈金瓶梅〉跋》曰:“《金瓶梅》一書,不著作者名代。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,憑怙奢汰,淫縱無度,而其門客病之。採摭日逐行事,匯以成編,而託之西門慶也。書凡數百萬言,爲卷二十,始末不過數年事耳。……此書尚無鏤版,鈔寫流傳,參差散失,惟弇州家藏者,最爲完好。余於袁中郎得其十三,於丘諸城(名志充,?一1632)得其十五,稍爲釐正,而闕所未備,以埃他日。……仿此者有《玉嬌麗》,然而乖彝敗度,君子無取焉。”(《小草齋文集》卷二十四,天啓丙寅,1626 ,葉向高序刊本)據馬泰來考證,“謝肇淛是在萬曆四十四年(1616)至萬曆四十五年(1617)這兩年內,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處借得《金瓶梅》抄本,並撰寫《〈金瓶梅〉跋》”(《諸城丘家與〈金瓶梅〉》,載《中華文史論叢》1984年第四輯,第l99一212頁。引文見第202頁)。
薛罔(1561一1641以後)亦是較早讀到《金瓶梅》者,他在《天爵堂筆餘》卷二說:“往在都門,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《金瓶梅》見示,余略覽數回,謂吉士曰:‘此雖有爲之作,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,當急投秦火。’後二十年,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,予得盡覽。初頗鄙嫉,及見荒淫之人,皆不得其死,而獨吳月娘以善終,頗得勸懲之法。但西門慶當受顯戳,不應使之病死。簡端序語有云:‘讀《金瓶梅》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,生畏懼心者君子也,生歡喜心者小人也,生效法心者禽獸耳。’序隱姓名,不知何人所作,蓋確論也。所宜焚者,不獨《金瓶梅》,《四書笑》、《浪史》當與同作坑灰。李氏諸書,存而不論。”(此書有薛三省天啓二年1622序,乃崇禎年間刊本)薛罔《〈天爵堂筆餘〉序》謂集中收萬曆二十三年(1595)至萬曆四十八年(1620)所寫文字,故知萬曆四十八年或稍前,薛罔已讀到包巖叟寄給他的,“簡端”有東吳弄珠客序的刊本《金瓶梅》。據其文集可考知薛罔於萬曆戊戌(1598)至壬寅(1602)年在京。所謂文吉士指文在茲(?一1603),文在茲於萬曆辛丑(160l)登進士第,“初授翰林院庶吉士,不二載,已終養歸卒”(乾隆《三水縣誌》卷十)。黃霖考出:“包巖叟,名士瞻,萬曆末由監生官德州判,著有《妄譚》一書。他和薛罔都是屠隆的同鄉後學。”(《〈金瓶梅〉成書問題三考》,《復旦學報》1985年第4期)薛罔讀到文在茲藏抄本,當在1600年前後。
對《金瓶梅》在從抄本到刊本流傳經過,記載得最詳細,且最多爲人徵引的是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中所寫的一則筆記:“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滸傳》爲外(應作‘逸’)典,予恨未得見。丙午(1606)遇中郎京邸,問:‘曾有全帙否?’曰:‘第睹數卷,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(?一1621)家有全本,蓋從其妻家徐文貞(名階,1503一1583)錄得者。’又三年(1609),小修上公車,已攜有其書。因與借抄挈歸。吳友馮猶龍(名夢龍,1574一1646)見之驚喜,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。馬仲良(名之駿)時榷吳關(萬曆四十一年,1613),亦勸予應梓人之求,可以療飢。予曰:‘此等書必遂有人版行,但一刻則家傳戶到,壞人心術,他日閻羅究詰始禍,何辭置對?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!’仲良大以爲然,遂固篋之。未幾時,而吳中懸之國門矣。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,遍覓不得,有陋儒補以刻入,無論膚淺鄙俚,時作吳語,即前後血脈,亦絕不貫串,一見知其贗矣。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,指斥時事,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,林靈素則指陶仲文,朱勔則指陸炳,其他各有所屬云。中郎又云:‘尚有名《玉嬌李》者,亦出此名士手,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。武大後世化爲淫夫,上烝下報;潘金蓮亦作河間婦,終以極刑;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,坐視妻妾外遇,以見輪迴不爽。’中郎亦耳剽,未之見也。去年(1619或1620)抵輦下,從邱工部六區(原注:‘志充’)得寓目焉,僅首卷耳,而穢黷百端,背倫滅理,幾不忍讀。其帝則稱完顏大定,而貴溪、分宜相構亦暗寓焉。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,則直書姓名,尤可駭怪,因棄置不復再展。然筆鋒恣橫酣暢,似尤勝《金瓶梅》。邱旋出守去(按:據考,應爲1620),此書不知落在何所。”(卷二十《詞曲》)李日華(字君實,1565一1635)《味水軒日記》提到:“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日(1615年12月24日),伯遠攜其伯景倩所藏《金瓶梅》小說來,大抵市渾之極穢者,而鋒焰遠遜《水滸傳》。中郎極口贊之,亦好奇之過。”沈德符於萬曆四十六年(1618)秋中舉後,年底上京。照此條記載,他在上京前已讀到“吳中懸之國門”的刊本了,則刊本之出現,當在萬曆四十五年季冬至萬曆四十六年底間。說此書於萬曆四十六年面世,大概是可信的。
就以上記載,我們可以看到,1592年後有抄本《金瓶梅》在文士圈中流通。1595年董其昌藏本由袁宏道傳抄。大約在1607年謝肇淛借抄袁宏道本,1616-1617年間借到丘志充藏本補抄,並寫了跋。據謝氏跋,董本和丘本《金瓶梅》都不全,且皆爲廿卷本。1609年沈德符又從袁中道借抄此書。當時還有王肯堂、王穉登和文在茲的殘本,有關這三個本子記載不詳,未知情況。此外又有傳說中的徐階、劉承禧和王世貞所存全本,前者下落不明,後者則在萬曆年間已失散。薛罔和沈德符都是既讀過殘抄本又在萬曆末年見到新刊本的人,照薛罔的引錄,他所讀的刊本首端有東吳弄珠客的序。從薛、沈兩人的記載,似乎他們沒讀到附在“十卷本”上欣欣子的序,因此對作者有諸多揣測。估計他們所讀的刊本是“廿卷本”,未必有插圖和批語。上面已指出,刊本大概在萬曆四十六年間出版,東吳弄珠客的批語,是爲“廿卷本”的出版而寫的,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“廿卷本”是崇禎年間再刊本。“十卷本”要在“廿卷本”出版後纔出版的,否則他不能收人東吳弄珠客的序。崇禎己巳(二年,1629)聽石居士的《〈幽怪詩譚〉小引》謂:“不觀李溫陵賞《水滸》、《西遊》,湯臨川賞《金瓶梅詞話》乎?”則“十卷本”應出版於1629年前,如此,“十卷本”在1619一1629年間出版。
上面我們研究萬曆年間文士關於《金瓶梅》的記錄,發現他們讀的,大致是“廿卷本”。沈德符在萬曆四十七年所寫有關《金瓶梅》的資料指出:“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,遍覓不得,有陋儒補以刻人,無論膚淺鄙俚,時作吳語,即前後血脈,亦絕不貫串,一見知其贗矣。”這個記錄,和現存的“廿卷本”相同。再加上薛罔引錄他所見到的是刊本,“簡端序語”是東吳弄珠客寫的《〈金瓶梅〉序》,和“十卷本”“簡端”有欣欣子的《〈金瓶梅詞話〉序》不同,使我們知道,萬曆四十六、七年間,“廿卷本”《金瓶梅》已面世。目前我們看到的“十卷本”,第五十三、第五十四回較“廿卷本”這兩回文字風格和內容有較大的差別,比其他各回,“十卷本”此兩回較接近原作。再加上其他校勘材料,使我們發現“十卷本”和“廿卷本”是兄弟本,而不是一般所說,“十卷本”刊出後,有人加以增刪改易,加上評語和插圖,產生“廿卷本”。兩本同出一源,都是《金瓶梅詞話》,“十卷本”較少改動,更忠於母本,保存了詞話的形式。“廿卷本”則已作大增刪,成了案頭讀物。比較兩本的第五十五至五十七回,可發現兩本相當接近。“廿卷本”這五回雖和全書其他部分不大相同,但這五迴文字風格相近,內容也有內在的照應關連。“十卷本”這五回書分成不大有關連的兩部分,第五十五至第五十七回有提及前兩回內容的地方,和“十卷本”的第五十三、第五十四回不相應,反而和“廿卷本”的這兩回相應。就是說,“十卷本”這五回有兩個不同的來源,前兩回近詞話本,後三回近“廿卷本”的母本。這三回“十卷本”文字比現存“廿卷本”多,不會從現存“廿卷本”拿來的,這是現存“廿卷本”對母本刪削的證例。至此,有關《金瓶梅》形成的歷史,照目前的研究,我們可作下列的描述:嘉靖年間有藝人創作並講演《金瓶梅詞話》,我們可以以萬曆二十六年李開先《寶劍記》出現爲參照點,在這之前《金瓶梅詞話》前半部已定形,在這之後《詞話》後半部也漸漸定形,最遲不會遲於萬曆二十年,很可能在隆慶或萬曆初,已出現抄本的《金瓶梅詞話》。文士間流傳的是“廿卷本”,缺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七回。後來有人刪削了其中的詞話成份,改寫部分文字,又補上所缺五回書,於萬曆四十六年出版“廿卷本”《金瓶梅》,有東吳弄珠客序,此爲“廿卷本”的母本。此一萬曆刊本《金瓶梅》,再經刪改,加批,於崇禎年間加繡像刊行,就是我們所說的“廿卷本”《金瓶梅》的初刊本,一般認爲可能正文已失佚,祇存下插圖的《王氏本》。以後的“廿卷本”本,如《北大本》、《天大本》、《內閣本》、《首圖本》、《上圖甲本》、《上圖乙本》、《天圖本》等等,都是崇禎“廿卷本”刊本的翻刻本。崇禎“廿卷本”批提及的“原本”,指的是萬曆刊“廿卷本”而不是它的底本詞話本。張竹坡評本第一奇書的各種本子,亦是自崇禎“廿卷本”刊本或其翻刻本來的。藝人創作的《金瓶梅詞話》,很可能是每十回爲一單元,合爲一卷。此本的一個抄本,也缺五回,在流傳中據演唱者底本,補人第五十三、四兩回,仍缺三回,祇在藝人圈中傳,此本有欣欣子序。可能在萬曆“廿卷本”刊本面世後,有書坊得到此一藝人流傳的抄本,參考已面世的刊本稍加整理,從萬曆“廿卷本”刊本補人所缺的三回書和東吳弄珠客序及廿公跋,刊出十卷本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,這就是我們目前能看到的“十卷本”。從《棲息堂本》第五回末頁與日光本、臺北本不同,可知此本刊印不祇一次。“十卷本”流傳未廣,除了明末的聽石居士和清初的丁耀亢曾提及外,一般都不知有這麼一種版本。清代以後流傳的都是“廿卷本”系統的《金瓶梅》,直到1932年此本重現人間,纔爲研究者注意。這是一個比較接近原作的《金瓶梅詞話》。
《金瓶梅詞話》各版本及其關係:
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十卷,卷十回,共一百回。簡稱爲“詞話本”、“十卷本”;因其中有“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”序,故又稱“萬曆本”。此書現存全本三部,殘本一帙。除一部藏中國外,餘藏日本。
山西本 1931年在山西發現,後入藏北平圖書館,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。缺第五十二回第七、第八兩葉。在原本上有後人用硃筆和墨筆加批、改字。改字有時在字上改,有時傍改。亦有在字上改了看不清時傍改的。保存甚好,未見損害。
慈眼堂本 現藏日本日光慈眼堂。缺五葉。有“因破損有文字泯滅處”,“有鼠害痕跡”(第五回);“第九頁匡郭切去一角,而棲息堂本完全沒有”(長澤規矩也《〈金瓶梅詞話〉影印本的經過》,載黃霖、王國安編譯《日本研究〈金瓶梅〉論文集》,濟南,齊魯書社,1989)。
棲息堂本 現存日本山口縣德山市毛利書庫棲息堂。缺第二十六回第九葉、第八十六回第十五葉和第九十四回第五葉。第五回末葉(第九葉)文字與慈眼堂本不同。“因破損有文字泯滅處”,“第九頁匡郭切去一角,而棲息堂本完全沒有”,“能看到的匡郭、界線、文字的破損,棲息堂所藏本也多一些”(長澤規矩也,《〈金瓶梅詞話〉影印的經過》,載黃霖、王國安編譯《日本研究〈金瓶梅〉論文集》,濟南,齊魯書社,1989)。“完全沒有外加的註記等,保存狀態也很良好,有些地方有蟲蛀的痕跡,但不影響文字的閱讀”,“卷首序跋的次序是:欣欣子的序、東吳弄珠客的序、廿公的跋、四貪詞。這一點,與北京圖書館本的跋和詞的次序正相反”(上村幸次《關於毛利本〈金瓶梅詞話〉》,載黃霖、王國安編譯《日本研究〈金瓶梅〉論文集》,濟南,齊魯書社,1989)。
京大殘本 存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,原爲《普陀洛山志》襯紙,存二百二十五面,分裝三冊。所存者爲第十一至十三、第十五、第四十一至四十八、第八十八至第九十四回,除第十一、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五、八十五、九十一、九十二回完整外,餘皆殘缺。“京都大學殘本中有不清或模糊之處。我看來此三本都依同一版而梓印,而京都大學殘本,應在此兩本之後”,“京都大學殘本的天頭處常夾有批語,而這些批語中有幾處已被‘腰斬’爲裝訂此書時(或裱入《普陀洛山志》時)所裁去……”(參見孫立川《京都大學所藏〈金瓶梅詞話〉殘本》,載《明報月刊》1990年9月號,第102一106頁)。
據比勘可知,現存四種《詞話》本皆同一版本,惟《棲息堂本》第五回末葉爲後刻補人者。據研究此本印行較遲,缺此一葉,遂據《忠義水滸傳》第二十五回補刻者。是知(詞話》本最少有兩次印刷。
古佚本 1933年馬廉等以“古佚小說刊行會”名義縮印山西本,所缺兩葉以白紙裝入。影印本增人通州王孝茲所藏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插圖二百幅及扉頁。書末加編號。首回首頁下方加蓋“古佚小說刊行會章”陽文小篆朱印。
單色印刷,山西本大部分硃筆批被刪去,小部分保留,變爲黑色。山西本上墨筆在正文字上改字在原本墨色有層次,勉強可分辨。影印本則不易分辨,故在底片上將原字修去,寫上改文。
山西本目錄及正文皆有絲欄分行,目錄及正文空頁處偶有絲欄,大部分沒絲欄。古佚本於各空頁一律畫上絲欄。
此本曾被多次影印,所缺兩葉,多據崇禎本補入。
大安本 1963年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據《慈眼堂本》和《棲息堂本》配合影印,並附《棲息堂本》第五回末葉。書前有凡例。書末附《日光本採用表》,列出所使用《慈眼堂本》葉次。此表說明第一條謂第九十四回第五葉採用中國國家圖書館影印本。又有《修正表》,於原本文字不清晰處,據其他各本校出。大安本以棲息堂本爲主,參用慈眼堂本及古佚本的百袖本。正文共五冊,第六冊爲《清宮珍寶皕美圖》。大安本曾多次被影印,但影印本多缺附錄部分。
聯經本 1978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以古佚本爲底本,又參考山西本套色影印。其尺寸則依山西本。插圖取自古佚本,但分置各回首。目錄及正文空頁的絲欄亦照古佚本。
聯經本據傅斯年藏古佚本校對山西本。將古佚本中原山西本朱墨批及點改處描爲朱墨,若干古佚本修字回改爲原字。再將校本複印兩套:一套爲黑色的影印底本,在上面塗掉硃筆部分;一套爲朱墨的影印底本,在上面塗掉黑墨部分,然後製成兩套底片。在塗改的過程中,由於工作失誤,有些原爲朱墨的變爲黑墨,有些原是黑墨的變爲朱墨。正文字上改字最難處理,爲了清楚,有時塗去改字,保存原字;改字補寫在原字字旁,和山西本、古佚本都不同。硃筆部分有時顏色較淡影印不清楚或影印不出,則據山西本描上,造成字迹不同甚或錯字,有些山西本的批佚去。
此本又據大安本補第五十二回第七第八葉。
此本前易古佚本扉頁爲聯經扉頁。修去古佚小說刊行會章加傅斯年章。又加《出版說明》一葉八則,其第八則謂硃筆批及校正皆據“原刻本一一還原”,與事實不合。
早在《金瓶梅》刊本還沒問世前,即有續書。寫於萬曆四十五、六年(1616一1617)年間謝肇淛《〈金瓶梅〉跋》末謂“仿此者有《玉嬌麗》,然而乖彝敗度,君子無取焉”。沈德符記他在萬曆四十八年(1620)從丘志充處借讀《玉嬌麗》。署“泰昌元年(1620)長至前一日隴西張譽無咎父題”的《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·序》及得月樓刊本署“楚黃張無咎述”的《平妖傳敘》都提及《玉嬌麗》,以後還有其他資料提及此書,但明亡後此書佚失。丁耀亢於順治十七年(1660)作《續金瓶梅》,以《金瓶梅詞話》爲前集,《續金瓶梅》爲後集。面世後,有人就將它和《玉嬌麗》混爲一談了。但照沈德符的描述,兩書除皆談因果報應一點相同外,其他內容相差甚遠。《〈續金瓶梅〉借用書目》中沒列人《玉嬌麗》,可能丁耀亢也沒有見過《玉嬌麗》了。在此稍後,出現了《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》四十八回。不題撰人,首四橋居士序。《隔簾花影》雖自稱爲“繼正續兩編之作”,而實爲《續金瓶梅》的刪削竄改本。此書後又改爲《花影奇情傳》等名稱出版。此外又有《金屋夢》,亦爲《續金瓶梅》的另一種刪削本。其詳細情況可參《〈續金瓶梅〉提要》。道光元年(1821)出現訥音居士(務本堂主人)編輯《三續金瓶梅》。訥音居士以《隔簾花影》爲繼《續金瓶梅》後的二續《金瓶梅》,故名其所寫之書爲《三續金瓶梅》。《三續金瓶梅》又名《小補奇酸志》,可知其所續者,爲張竹坡評本《金瓶梅》。《張評本》前有《苦孝說》,謂“作《金瓶梅》者,一曰含酸,再日抱阮,結曰幻化,且必曰幻化孝哥兒,作者之心,其有餘痛乎。則《金瓶梅》當名之曰‘奇酸志’、‘苦孝說’”云云。
《金瓶梅》譯本甚多,最早面世的爲署“康熙四十七年(1708)五月穀旦序”的滿文刊本。昭槤(1776-1829)《嘯亭續錄》卷一《翻書房》謂:“……及定鼎後,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,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,無定員。……有戶曹郎中和素者,翻譯絕精,其翻《西廂記》、《金瓶梅》諸書,疏櫛字句,咸中綮肯,人皆爭頌焉。”則又可知滿文《金瓶梅》爲和素所譯。此書中、日、美、法、俄諸國,皆有刊本或抄本。日文譯本最早出現的是罔南閒喬的《金瓶梅譯文》,百回,祇有抄本,大概祇是摘譯節寫。江戶末期曲亭馬琴(1767-1848)改編《金瓶梅》成《新編金瓶梅》。1882一1884年松村操翻譯的《原本譯解金瓶梅》爲日本最早的翻譯本,祇出版九回。以後陸續有譯本出版,亦皆不全。直至1949年,纔有尾板德司全譯本出現。1960年出版的小野忍、千田九一合譯的《金瓶梅》,採用詞話本爲底本,被認爲最好的譯本,此本曾多次修訂出版。在此前後還有出版多種全譯或節譯本《金瓶梅》。1853年法國巴贊(A.P.L.Bazin)發表《金瓶梅》第一回譯文,以後出現其他文字的部分譯本。1912年喬治·蘇利埃·德·莫朗(George Soulie de MOrant)出版編譯的《金瓶梅》爲《金蓮》(lotus d'or),以後還有英文、德文等《金瓶梅》節譯本。1931年出版弗朗·庫恩(Franz Kuhn)的德文節譯本影響最大,此書曾多次再版,又被轉譯成法、英等多種歐洲文字。克萊門特·埃傑頓(Clement Egerton)的英文全譯本於1939年出版。以上都是據張竹坡評本翻譯的。1977年莫斯科出版馬努辛(B·Mahhyx)的《金瓶梅詞話》俄文全譯本。雷威安(Andre Levy)的《金瓶梅詞話》法文全譯本在1984年出版。芮效衛(David Tod Roy)近年在美國出版英文全譯本。金龍濟的朝鮮文譯本據張竹坡評本,1956年出版。越南文譯本則以中國坊間刪節本《古本金瓶梅》譯出,譯者不詳,1969年出版。
(陳慶浩)
——以上摘自石昌渝主編《中國古代小說總目·白話卷》(山西教育出版社西元2004年版)。
香港三聯書店有會校本,當即此文本。按原文本「閒」多作「閑」,今爲便於分別,多有改動,如將「幫閑」改爲「幫閒」,「等閑」改爲「等閒」之類。每回前之繡像,本站取自臺灣增你智版《金瓶梅詞話》(其底本爲萬曆丁巳本《詞話》,《詞話》原無插圖,出版時于每回之前補入崇禎本繡像。)。
 粤公网安备 44512202000019号
粤公网安备 44512202000019号